文|呂岱如
"Politics is when you create a kind of stage where you include your enemy."
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關於「中心」的概念,我想嘗試用不同向度的意義來拉開討論的軸線,再轉談藝術中心的概念以及楊俊的計畫《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台北(提案)》,希望能夠透過展延不同層次的理解,來翻轉幾種「中心」的政治意涵,和對於藝術中心的想像。
若以拓墣(topology)的概念來思考中心,那麼中心或中心的結構也不過是一種情境,一種以單一或數個因素質量來將比較對象的全體作相較性的差異對照,一個暫時性的結構呈現。這個情境所表示的空間或結構僅作為一種可能的推算結果。舉例像此藉東京地鐵圖所表現的網路潮流圖。[1]地鐵圖本身即是拓墣地圖,利用其原圖的網絡關係再加以雙關意義比照網路潮流的關係,若觀看全圖,可發現性質各異的網站如Wikipedia, MSN, Youtube, Google, Yahoo等都各據一霸自為交通樞要。

Web Trend Map © Information Architects
又從社會學的論點來看,中心與邊緣的空間劃分事實上指涉經濟為政治、軍事、貿易等各種力量所造成的生產模式差異。中心與邊緣的關係說明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過程,其中由市場主導的經濟力量將形成所謂的中心。相反的,在相對邊緣的地區,其生產與分配系統卻有可能仰賴非市場經濟的因素決定,像是宗屬關係(kinship)等。再演繹,這個中心與邊緣的分野並非二元的對立關係,而是生產系統仰賴的來源是否僅為資本或亦其他相異的力量方為其決定因素。而「差異」正如在杭席耶對政治的闡述中是形成政治關係的要素,更是政治主體性的先決:也就是說,政治主體在政治關係中方為可能,並且可被定義在一種行動模式和所參與的相對歷程。[2]
這幾種思考何謂中心的線索,或許可以引導至一種理解中心(或邊緣)的概念的方式:差異的主體性若可被認知,就可以從這個主體性展開政治關係,以其特質獨有的生產方式、行動模式作為其政治力的來源,甚至成為所謂的中心或是邊緣。也可以說,政治力的運作則是在主體與其相關對象共同在一個舞台上爭豔其差異的主體性而呈現出來的。
假探索這些不同層次的差異作為途徑來試圖想像一個當代藝術中心的主體,也就是進一步思考當代藝術中生產與分配的經濟問題與其背後對應的政治、社會成因分佈的景貌與網絡,或甚探討在地獨有的各種非市場經濟因素如何支持這個現有的模式運作系統。中心的形成具有高度政治性意涵,即使是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其意味著一個高政治力的藝術、知識生產與分配系統運作,也代表其在文化場域裡的位置有一定之獨特性。無論其匯聚的專業度與取樣代表性,其展現的行動和經歷的相對外部關係運作將彰顯這個中心的主體性和政治力量,由此才衍生討論其功能性與目的。
以此思考來觀察楊俊的計畫《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台北(提案)》,可以更深入分析這些異同點以論在地政治的現實。如藝術家本人所言:「台北沒有當代藝術中心」,台北的確沒有這樣一個強而有力的藝術機構可以不藉官方資源並有實質力量成為藝術生產、論述、評論累進生成的中心來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且所謂的專業藝文從事人員站在生產者的立場也沒有相對的權力介入文化生產的政治關係裡,反而往往在這個政治關係裡缺席。不只藝術生產者於在地政治環境的邊緣性,台灣自身亦處於全球藝術文化版圖裡的邊緣位置。楊俊在一種好奇又興奮的外來身分裡被此等現狀激發,以社會介入的藝術行動來促發此議題的思考和更多行動上的可能串聯,數個月內,聯合舉辦YTA的戶外派對、集結四十多位藝術專業從事人員進行一個週末的研討會來討論這「一個當代藝術中心」的可能提案、在典藏今藝術雜誌上製作一個相關主題特刊等。這些大動作進行的同時,他並不諱言他在此案上的天真態度:這個藝術行動在多個實踐階段內都在提問與提議,而非試圖提供任何答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特殊外來身分在這裡則是有力的支點與工具,這份差異直接讓這個藝術創作行動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相對性運作力量來召集當地藝術社群的投入,讓他有一個特殊的政治力量,而計畫的參與者在不同過程與階段性的結果中面對赤裸的差異--建立在對自身政治權力邊緣性的認知。另一方面,這裡有一個集體慾望的聚合,投射一種透過這類集結而可能將具有實質政治力的主體存在。這份認知與批判的態度成為這些聚會的主要也是唯一的共識基礎。
這個集結在三天的週末聚會裡,確實造成了一個暫時性的「中心」;期間的運作行動與生產機制方式皆非常態,且行動具有某個層次上相當高的政治主體性,各路人馬的匯聚產生了一個舞台,所有論辯就是一種主體性的彰顯。然而,就針對「一個當代藝術中心」的形成,也就是如何利用這個社群特有的藝術實踐系統運作與所謂官僚體系所構成的權力系統產生差異性的抗衡,以及尋找這個中心之於全球版圖的對話位置,並且將這個藝術實踐中所涉及的資訊、知識、勞動、生產、交易、分配等過程除了做一個與機構上的分野,也進一步在定位上有不同的設定和運作等行動模式上的問題討論,在聚會的討論中卻無法聚焦,也在日後所有的討論中消失。這樣的階段性結果事實上呈現了一個去中心的中心,也說明此事件僅有批判的類運動性行動出現,尚未能合力造成一個比官僚體系更具獨特性的生產系統。更精準地說,目前這個社群與官僚體系的共生現實纔是值得深究的議題;這個社群的行動模式與官僚體系並無相對差異纔是沒有主體性的根源。
在如此現實底下,楊俊個人最後在典藏今藝術所發表的三種對台北當代藝術中心提案或多或少提供了跳躍性的思考方向,也就是提出了一種與現實絕對差異的可能空間。提案之一是建立一個有如百貨公司的當代藝術中心,此結構有別於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產官學全包的經營方式,並且對當代藝術的經濟模式提出超越性的想像,創造獨立、不再仰賴官方資源的經濟模式後,當代藝術社群當然就有與官僚體系切割的可能,而這個藝術中心也明顯地與美術館、畫廊系統、拍賣會、博覽會的形式不同,其欲建立的是以藝術實踐為軸而進一步介入社會各種資本、市場運作的消費系統裡,藝術實踐的行動模式就成為藝術社群主體性建立的捷徑。另一個有趣的提案則是建議將此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直接設立在台灣以外,這樣的做法或許可供參照的範例是瑞士文化中心(The Swiss Institute)。分別設立於紐約與巴黎,瑞士文化中心卻從未以國家主義、國族符號再現,或僅推動瑞士藝術家的作品為運作方向。與後帝國主義情節頗深,致力推動本國文化的英國文化中心、哥德學院(德)等海外文化機構有顯著的差異,瑞士文化中心的主體就是當代藝術實踐的推動與文化交流,其經營團隊有絕對的自主性和專業度,並非各種官派人員。甚至像是瑞士藝術家在這些海外的文化中心來做對於瑞士的批判作品都曾大方地發生過,這裡不會有強要藝術文化作為一種正面積極國家形象的審查與約管,而藝術實踐的自主性、批判性都得以自由開展。若台北或台灣成立了類似的海外機構作為當代藝術中心,這個做法的確提供一個直接不過的跳板,該中心的對話對象就是國際都會城市裡匯聚的文化活動參與人士,略過種種內部與外部的疆界問題和地緣限制,橋接更多的面對面的交流,並且這個對話的位置本身就建立了不同的行動模式--透過出走,這個中心不在我們之中,而是一個與外部對話的適度位置。
本文無意陳論《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台北(提案)》作為一個社會介入事件的成敗。就其產生的事件來看,YTA的活動為不同學院的學生做了跨派系的串聯交流;週末聚會產生了一個後繼無力的網路平台[3]、無法宣告的宣言、許多異質想像與期待的衝撞,以及可供懷舊的十五萬字的聽寫稿記錄與照片;最後的特刊則集結了更多各界的觀察和楊俊自身對此議題想像的藍圖,也促發本刊物創刊號在這個議題上的對話。這個計畫造就了非常多不可能的對話與聚合,也留下一個短暫的去中心之中心的大合照!若從藝術實踐和美學政治的角度來思考,這個作品所聚合的政治力或是中心情境應該比艾未未的《童話》在上屆文件大展所集合的1001位中國人[4]所達成的還來得偉大而困頓。
藝術中心的問題不在於它是何種模式、如何操作、或它擁有多少資本、坐落何處,而是其政治力的主體性是否與藝術發展的自主性相輔而在整體的文化場域中有其生產模式上的特殊優勢。而事實上,藝術的邊緣性也可以用此類比的方式理解,並且嘗試去思考這些之所以邊緣的差異性主體可如何成為反逾現實的政治力量。若幹不成某種中心主任,那搬張椅子來當角頭老大是否也是掉入一種永恆草莓園[5]的觀點置換法?
[1] 由日本的Information Architect繪製,此圖為2007年版本之局部。歡迎至其官方網站下載最新版全圖。http://informationarchitects.jp/
[2] Rancière, Jacques. Ten Theses on Politics. Theory & Event - Volume 5, Issue 3.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http://anartcenter.ning.com/
[4] 艾未未,來自北京的藝術家。在第12屆文件大展展出作品《童話》,找了3000萬元人民幣的贊助,招募1001位中國人前赴德國卡賽爾參展,引發相當大的討論。藝術家的個人部落格網站: http://blog.sina.com.cn/aiweiwei
[5] 挪用披頭四的歌曲名稱"Strawberry Field Forever", 原曲由John Lennon所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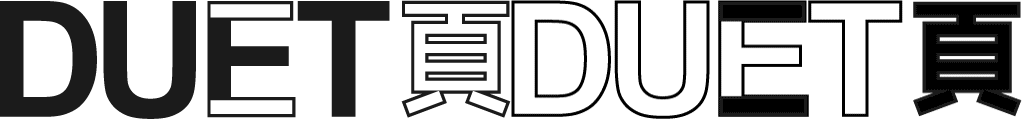
很棒的刊物,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