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鄭慧華
新自由主義在英國柴契爾當政時期,被稱作「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別無選擇」,這亦是柴契爾當時的名言,意即「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外,其他皆無可能」。柴契爾領政與美國雷根時代以來所力倡的自由市場運作及其價值觀,在冷戰結束後更以所向披靡的態勢掃向世界,歷經了全球化,這句話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型態,亦適合描述今日台灣的整體社會,甚至包括當今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發展邏輯。台灣政府向新自由主義看齊,文化推動亦不自覺地逐步走向新自由主義下的產業市場法則,文化與文化知識的生產逐漸以產值、績效、品味市場性(受歡迎程度)為競爭和評斷基準,走向單一與扁平的思考。所謂「文化經濟」在缺乏深刻思辯之下成為文化發展之表面托辭。而當下政策既出便得立即見效,被要求以資本市場邏輯運作的文化生產終致淪為一場又一場101煙火秀。
煙火秀耗資龐大、瞬間即逝,徒具炫麗表相卻不留下任何值得思索的內在,這已與文化推動本應具備之引根深扎的目標背道而馳─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卻是我們當下最大的困頓所在。 煙火秀中有的是萬頭鑽動的參觀人次,可以讓業績破錶並交出漂亮的執行報告,但煙火秀讓眾人讚嘆了三分鐘,之後呢?「文化產業」以行銷、節慶、觀光為文化品味的形塑基調,不但逐步破壞與磨滅文化深耕的本質,還讓需要長期累積與滋長的紮根工作比以往更加難以生存,而在這參雜各式政治性目的及商業利益的生產關係中,藝術界今日是否還有改造我們所處的現實的力量?
華裔奧地利藝術家楊俊於2008台北雙年展中提出《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台北(提案)》計劃,於2008年12月的一個周末邀請了四十多位藝術專業工作者參與,在「一個當代藝術中心」的廣泛概念下展開關於觀念、策略和實踐上的討論,「提案」一詞似是希望引發談論關於「理想的」、「符合當代社會和創作觀念轉進」之需求的機制和概念為何。不過兩天下來,從基本的溝通、互訴各自所遇到困頓開始,僅結束於大家彼此心中化約出的幾項抽象概念。弔詭的是,若這個「提案」計劃對台灣藝術界的召喚力是來自於它的理想性,討論會現場表現出的無力卻也反諷地來自它的「理想性」。與會發言者就各自所處的位置所提出之對藝文生態的反省與觀察,使大家逐步拼湊出當下的整體文化圖像,但在這之中,現下機制中的生產關係鍊被描繪得越是清楚,深陷於其中的藝術專業工作者越感到無力反擊。
重點已不在於「一個當代藝術中心」的提案為何,而是在國家機器運作下的政治文化意識型態、政策乃至於資源分配方式其實已經決定了我們能對自身有多少想像。換句話說,若這樣的集體處境未被充份意識到,那麼探討其所衍生之片面或局部性的制度和結構性問題,當然也只能以矛盾和無力感收場。也許該直接這麼問:在資本主義之市場價值全面主導的環境裡,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及其概念可還有「另一種選擇」?
答案其實已很明確,當代藝術中所關注之「文化政治」及其中文化主體所應具備之能動性,已被「政治的文化操作」所架空,只是我們是否願意承認現下所謂「多元」、「豐富」之假相下的空洞和悲劇?
當我們回溯文化機制背後之生產關係的依存和矛盾,幾個熟悉的例子猶在眼前:首先是台北華山藝文特區,其招標運作下的文化與商業利益之衝突和矛盾;台北當代藝術館(MoCA)依附於模稜兩可的政治要求和票房要求,致使一座號稱「當代藝術美術館」的專業內涵失焦,不見推動藝術文化之原初立意,也看不到一座美術館對文化之長遠定位與使命,只剩下媚大眾之俗、尋求立即業績之表現而走向徒具形式的操作;即將正式營運的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在成立之際,旋即又落入「公民(大眾)美學」或「小眾菁英」之文化品味上或文化消費之假命題的粗糙定位爭議;接著,2010年,傾國家之力全力推動的花卉博覽會的龐大工程與規劃,即將強勢介入台北市立現代美術館展場......。從中央到地方,這些個案檯面下的政治與政策影響力,以及檯面上浮現出的專業性問題,其實十分雷同。而文化藝術生產被統合在政治和經濟目的的考慮下,走向以觀光和節慶的消費文化表相來誘惑和麻木群眾, 藝術文化的歷史脈絡和專業自主性在此之中逐步淪喪。
僅管我們都知道觀念開發與歷史建構是現在最為迫切的工作,然缺乏改造或反抗當下政策走向的動力,則沒有改變的可能。建構工作尚未開始,倒錯的藝術產業化、文化產業化之鼓吹與執行卻又加速文化本質的被排除和掏空。台灣官方作為倡行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小政府,事事號稱以大眾利益為依歸,說穿了只是怯於輿論而全力媚俗。當今官方民間皆落入「文創救國」之意識型態陷阱,天真地希望以數十年前台灣發展外銷產業、電子產業的相同邏輯再「複製」出另一個產業的勃發和台灣的「(文化)經濟奇蹟」。政府盲目地以為如此便能重建人民信心,快速建立文化主體性,甚至以此刻意遮蔽台灣長期以來在國際政治、全球經濟位置上的邊緣化,刻意遮蔽產業發展在時代變化中興起與衰落的真相。無技可施之下幻想著文化創意產業能使台灣擺脫「代工」形象,以短視近利的想法、以行銷口號來安撫集體的失落感,讓全民在各種政經利益的趨使下共同製造出各種文化泡沫和社會幻像,並又以此作為規避責任的更大藉口。
就「一個藝術中心」的實踐來說,作為最大的利益團體,我們的政府十分樂意也擅長供養建商和承包商,發包各項大型工程案,在各地方建立一座座醒目且龐大的硬體設施。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從不缺「文化中心」、「藝術中心」、「藝術村」或各類「園區」...這些徒具外表但內在空洞的「場所」。多數民間企業或個體則是在商業價值與利益趨使、內在缺乏信心的匱乏意識籠罩下快速接納文化速食主義,與政策結合並樂於承攬作為下包以分得一杯羹。
「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價值外,其他皆不可能。」─這也是我們當下的文化危機。而政府帶頭製造巨大的泡沫的另一種結果,便是讓自己自溺地陷於「國際化」的假象中。如此一來,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於地緣上成為「中心」、或生產更多的「中心」則成了這個廣義的議題下更大的自欺和反諷。當我們早已不存在文化真正的本質和內在,討論則在窄化和空洞的文化政治意義中落入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爭論。事實上,這也不只是制度或結構上的問題,其根源更是一連串政治經濟運作的過程與長期心理徵候表現的結果。我們必須體認到,若無關整體和缺乏外部真實的參照,無論是概念或制度上,「中心」的討論為何並無意義。文化藝術工作者現今的困頓與不滿,在於我們面對如此的現實時所進行的任何討論都將失效;任何一個理想的概念或文化場域之形成,也都無一可免於被這個不斷由資本所主導的「幻像生產機器」給消耗殆盡。
事實上,我們要的解答也很簡單:如何得以讓藝術文化深化、建立其歷史性脈絡,如何真正建立起當代所應當具有的專業性,並真正具備能力面對「國際化」的問題?然要實踐這清楚具體的解答也就是今日最大的難題。文化藝術產業化所引發的誤謬如今已深入社會每個面向,甚至包括教育系統,它潛在影響著尚未踏進社會的青年學生,給予他們對未來和文化的錯誤想像和期望,這當然同時是學院教育所該警覺的危機,當負起責任從思想上進行由下而上的基礎改革工程。否則,我們也別無可能。
行動主義者Susan George提出對TINA的反抗:TATA(There are thousands of alternatives)─「我們有千百種選擇」。在政治、經濟和媒體文化各個領域裡,我們看到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中所提出的千百種訴求與行動策略,也看到媒體行動者反對今日主流媒體宣傳、商業廣告的各種串連與自覺,然今日資本主義全球化為世界所帶來的生活災難與我們所將付出的代價,是否也可以為我們同時帶來文化發展之社會實踐的省思?無論西方或亞洲,無論從哪一個脈絡出發,今日我們都面臨相似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後該質問的是我們是否依然要繼續為此文化生產之政治意識型態與操作買單?個人、企業到政府又如何能夠從教育、體制內外或根本「態度」上面對這巨大泡沫之真相?答案很直接也很明白:唯有先從企圖以台灣製造業模式再創「文化產業奇蹟」的妄想中脫離出來,才能夠保有文化風景中原本應有的豐富光譜與不同深度,並看見新的契機。如此,對於要談論並實踐理想中的文化藝術機制,或聚焦「一個當代藝術中心」,我們何嘗沒有千百種可能和千百種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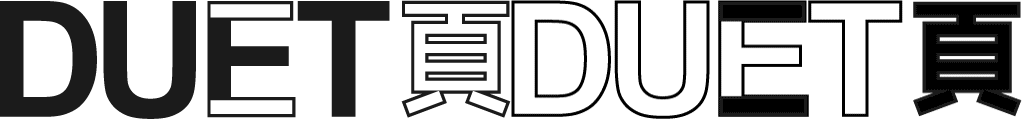
留言